對于喜愛法國文學作品的多數中國讀者而言,余中先一定不是個陌生的名字。他像是一條隱秘而堅韌的航道——四十多年來,他把百余部法語作品通過翻譯“擺渡”到漢語世界,也把自己活成了法國文學在中國的一張“活地圖”。
而這條航道的起點,正是他書房里一張背窗而放的書桌。如今已經退休的他,每天依然雷打不動準時落座工作,開卷譯事。陽光從他背后漫過肩膀,悄悄地給右手墻邊那一排排擺放得滿滿當當的書墻鍍上一層柔和的金光。書柜里,有這些年來余教授自己翻譯過的書,有詞典這類工具書,還有別人送來的珍貴外國老版書。書墻一直延伸到客廳的走廊上,像一條不肯靠岸的船,隨時準備把下一部未被發現的法語作品泅渡到漢語的彼岸。
日前,由余中先所著的《從荒誕到反抗:導讀加繆〈局外人〉和〈鼠疫〉》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本報記者借此機會與余中先教授進行了一場獨家專訪,聽他在這張書桌前分享自己如何以譯筆為舟,載著冷門經典“逆流”而上的往事;又如何看待靜水深流的文學之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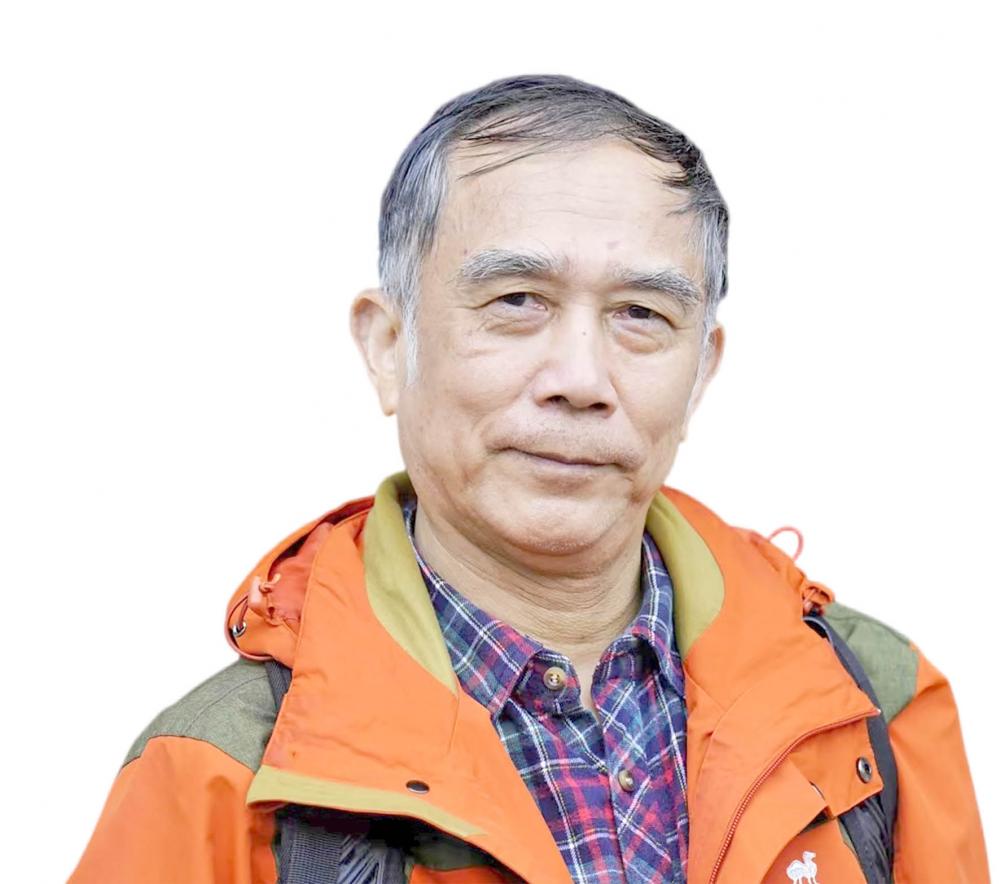
余中先。資料圖
推開文學相遇之窗
回顧余中先教授過往的翻譯史,不難發現他曾經著手翻譯的眾多法語文學經典作品,也是不少中國讀者與遙遠的法國作家們“初識”的契機。
1985年,余中先從北京大學法語專業研究生畢業后,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世界文學》雜志社,從事外國文學的編輯工作。那時,《世界文學》幾乎是中國讀者眺望世界文學的“第一扇窗”。而余中先憑借對文學的熱愛與法語專業積累,除了完成編輯的職責之余,也嘗試翻譯更多的法國文學作品。他在選擇翻譯文本時,尤其擅長發掘法國文學作品中的“冷門寶藏”,有著超越時代的文學洞察力和精準判斷力。
1988年,余中先第一本正式發表的譯作——弗朗索瓦絲·薩岡的《你好,憂愁》問世。這本寫盡青春期迷惘的小說,初時發表反響平平,直到2006年重版后卻得到了眾多中國讀者的喜愛。在他看來,這是因為聚焦兩代人代溝的問題在中國出現得比法國晚,所以相關的文學作品被讀者接受也就來得較晚一些。后來,他又把法國詩人、劇作家、外交官克洛岱爾也帶進了中文世界,讓漢語讀者第一次讀到“堪與莎士比亞的劇作媲美”的《緞子鞋》里的東方意象。2001年起,余中先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的評選工作,選出的作家如讓-馬利·居斯塔夫·勒克萊齊奧、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安妮·埃爾諾等在后來獲頒諾貝爾文學獎。
于是,一扇又一扇窗被悄悄推開——隔著時差與語種,讓“遙遠”的他國文學從此有了體溫,也讓“初見”成為了更多讀者愛不釋卷的“久別重逢”。
譯者的“三重門”
從事法國文學翻譯四十多年,又譯介過上百部小說、戲劇和詩歌作品,對余中先而言許多作品的翻譯過程都有著曲折奇趣的小故事。在這之中,“折騰得最厲害的”并最終成果能讓他感到滿意的作品,要數19世紀法國小說家于斯曼所寫的小說《逆流》了。
這本小說講述了作為貴族后代的主人公德塞森特,他厭倦了早年在巴黎的放蕩生活,便幽居到郊區鄉下買了一所宅子,過著一種被當時和后來的人認為是“頹廢主義”的生活。這本書里雖然沒有連貫的故事情節,但是作者努力用各種文字表達來描述主人公的豐富聯想:德塞森特為每一種利口酒的滋味都類比一種樂器的音色,像是苦味柑香酒相當于單簧管,薄荷酒和茴香酒則像長笛;還對自己豢養的一只烏龜精心裝扮,為其背甲鍍上華麗的金殼,又在背甲上裝飾珍貴的寶石。這本書以極盡感官之能事、辭藻華麗到近乎奢靡的“頹廢美學”,將沒落貴族世界的頹唐與精致一并封存于紙頁。
而余中先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關注到這本小說。法國《讀書》雜志的專家團隊早年曾在難以計數的圖書中精心分類遴選出一批個人理想藏書的書目并做成讀書專題,最后這些專題被集納整理為一本名為《理想藏書》的圖書,以便為世界各地的讀者提供一份全球經典閱讀指南。當年余中先首次把《理想藏書》翻譯過來后,就有人對照所選的法國文學篇目,發現有那么幾本書尚未有中譯本。其中,就有于斯曼的《逆流》。
余中先帶著疑問去查閱了這本書,恍然發現這本小說要翻譯過來確實存在較大的難度:書中不僅涉及到自然現象、社會生活、藝術現象、私人生活等各個領域的話題,還用了大量精巧華美的語言描寫了當時走向沒落的貴族社會歷史風俗和享樂生活,可謂是那個時代的“文化百科全書”。也因為如此,這對譯者的知識背景和文字語言水平的要求也相當高,讓不少譯者望而卻步。于是,他索性擼起袖子自己上:2008年動筆,2010年交初稿,邊查資料邊做注,給這座迷宮配上了鑰匙。
在他交付初稿的同一年,另一出版社剛好搶先推出了這本小說的國內首次中譯本,書名譯作《逆天》。但經過仔細驗證并結合文本分析后,余中先認為《逆天》的譯法更像是為了靠近年輕讀者閱讀習慣而選擇的用詞,“這種時尚的用法并不適合該歷史時期人物所表現出來的生活態度”。他認為,主人公隱居時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自己與自己較勁”,屬于一種“逆行倒施”,但還未至于大逆不道的“逆天”,因此他堅持將書名翻譯成《逆流》。后來他繼續尋找并參考了多個版本的資料,不斷優化譯本初稿,還趁著訪問法國的機會游歷了與于斯曼有關的幾處景點,才最終磨出了《逆流》的中譯本。
在余中先看來,對于譯事三難“信達雅”這三重門人們已經有過許多的討論,而這三個字中如果能把“信、達”做到位,也已經是一份合格的翻譯;至于雅與不雅,則要視乎文本的需求而定。他說,譯者的任務就是:“理解,努力地理解,努力地讓讀者跟著你來理解。”此處的“理解”本身已經包含著豐富的內涵:比如,故事來龍去脈是否清晰、細節是否清楚無遺漏、人物性格是否遵從作者意圖、時代特征有否交代、文字特色有否呈現等。
余中先表示,翻譯是要讓讀者更多地去接近原作,不能單純考慮譯本是否易讀,“譯者是要帶領讀者去努力適應原作的內容和形式。”他尤其強調,譯者不能因為原文的文字粗糙,在翻譯時就自作主張把中文改“雅”,“這會讓讀者在譯本里‘只見譯者而不見作者’”。
文科并非無用
談起自己寫的新書,余中先說自己與加繆的緣分早在大學時代就已結下,他畢業論文研究的正是加繆的《鼠疫》。四十年來,加繆筆下的人物和思想,始終是他反復咀嚼的精神養分。而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在聽過他的一次講座后,敏銳地意識到:這位資深譯者對經典的獨特解讀,或許能成為年輕讀者啃下“名著硬骨頭”的一把鑰匙。雙方一拍即合,余中先也欣然提筆,將半生研讀加繆兩本重要代表作的心得,合為一本“不帶學術架子”的文學導游手冊——這便是這本導讀新書的由來。
翻開這本小書,最直觀的感受是“輕”:書中文字簡練清晰,沒有繁重的術語理論,也拋開了冗長的理論。讀者可以輕松地走進加繆的故事,甚至對書中那些格格不入的小人物多一份耐心的觀察、理解和寬容。或許,這就是余中先最想遞出的“鑰匙”:不必先弄懂“存在主義”這些過分抽象的概念,也不必急著給人生下結論,只需跟隨里厄大夫去看病、跟著默爾索走上法庭,先看見“人”本身。然后就會發現,曾經高高在上的名著閱讀起來原來也可以如此輕盈,卻又如此結實。
余中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文科最大的“用”正是其“看似無用”。他表示,文學作品能展示人間萬千活法。面對荒誕、虛無、意義感缺失,加繆筆下的里厄醫生驅除無用的疑慮,只管埋頭救治病人——這些故事像一面鏡子,照見人如何守住本分、尋找微光。理解世界的復雜與他人的孤獨,這本身就是一種深刻的力量;哪怕只是一次短暫的共情、一次對陌生命運的凝視,“無用”之思也能抵達深邃的港灣。
在采訪的最后,回想起自己在中法文學翻譯之間的“擺渡”的五十年時光,余中先教授謙遜地笑著把這份堅守解釋為:“我不會干別的,就會干這個。”五十年只做一件事,在余中先看來不過是“坐下來就成了習慣”。每天上午三小時、下午三小時,他準時把自己放到那張背窗的書桌前,像把一枚硬幣精準地投進同一個投幣口,投進去的是法語的聲母韻母,掉出來的是漢語的字字珠璣。他說,翻譯就是“把法國的好東西拿過來給中國人”,而法國文學那股“標新立異又追求極致“的勁兒,恰好成了他繼續磨這把刀的理由。
對余中先來說,五十年如一日的擺渡還在繼續,對岸是仍在生長的法蘭西文學,此岸是愈發遼闊的中文世界,擺渡的人在來回往返,“一任潮水來去,他自獨馭蘭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