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寧
人們對一國國內的流動性知之甚多,流動性是金融市場中的一個基本概念,它通常表示在不顯著影響價格的情況下買賣資產的難易程度,較高的流動性有助于市場的穩定,而低流動性則可能導致波動性和低效率性。而《資本戰爭》這本書主要致力于探討全球的流動性,由英國邁克爾·J·豪厄爾(Michael J.Howell)所著,該書對全球“規模高達130萬億美元的資金流動池”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認為這些資金流的跨境流動既代表著“聰明錢”對經濟機會的跟隨,是資本逐利的結果,又可能同時會帶來巨大風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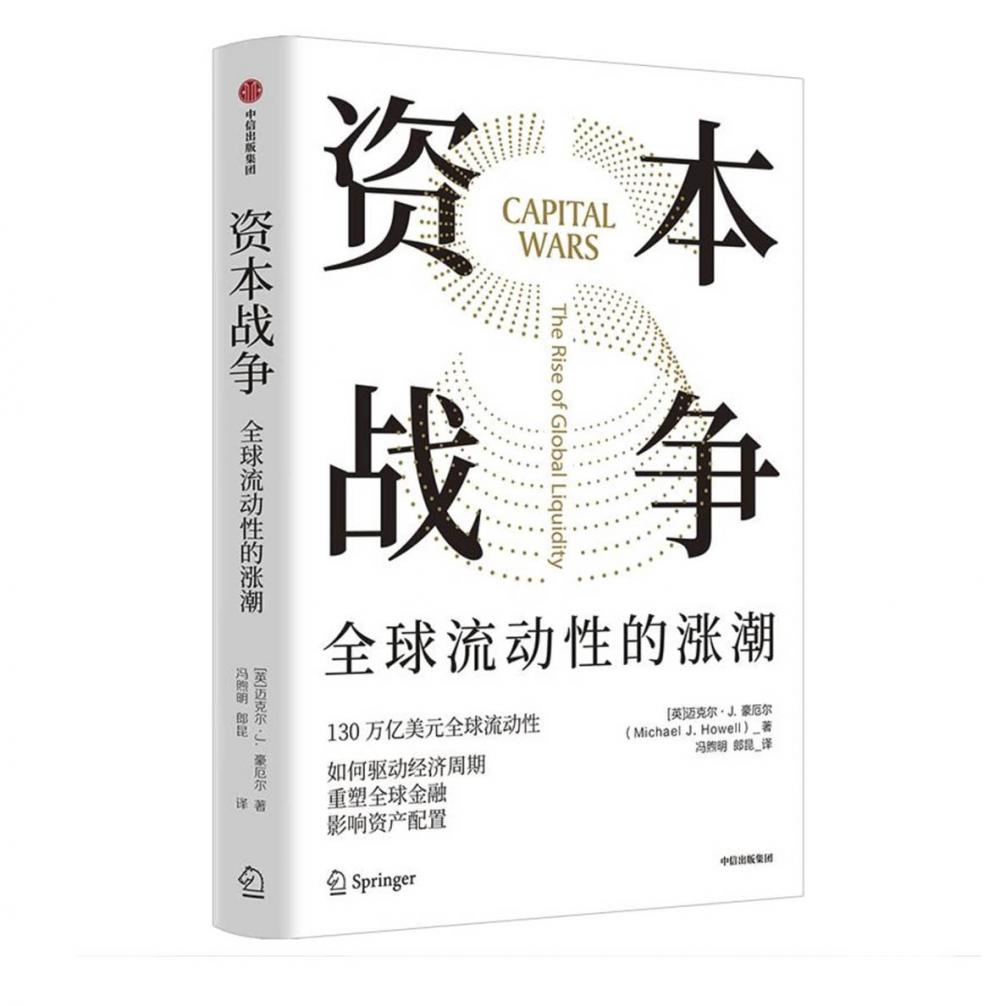
全球流動性講述的是通過全球銀行體系與貨幣市場流入的信貸和國際資本的總流動。自從上世紀80年代后,各國放松管制、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及主張較少的市場干預,共同推動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大幅增長,隨之而來的世界貿易及全球化的發展又助力了這一趨勢。作者從“全球流動性”這一概念出發,對當前全球經濟金融領域許多前沿的熱點進行了富有見地的剖析,其中包括了全球貨幣體系的演變、上世紀英美等大國之間的權力迭代、一國工業興起帶來的世界格局變化、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帶來的新變化、中央銀行的作用、影子銀行的角色、跨境流動背后暗含的地緣局勢變化等等。
作者還十分明確地提出了經濟周期主要是由儲蓄和信貸的數量驅動的,即資金流,而不是由高通貨膨脹或是利率水平驅動。作者還強調流動性的數量和質量兩個維度,不只是看數量,觀察質量同樣重要。作者坦言,相對于貨幣數量論,他更愿意從貨幣質量論去考慮問題。比如私人部門的債券與國債在安全性上有根本的質量差異。這一點是毋庸贅言的,現實中投資者們也是依據此原則來身體力行進行投資的,比如美債、日債等都是全球投資者熱衷投資的較安全資產,一國民眾對本國的國債也具有較大的信賴度,而公司債的安全性則相對國債略微遜色一些。
作者認為,在經濟繁榮和上升周期借入的錢,與在經濟衰退和下行期借入的錢,在性質上是不同的。但是,傳統的金融數據分析例如M2、社融、宏觀杠桿率等總量指標并沒有區分這一不同。作者還認為,不要只是盯著流動性的凈流入,也需要觀察總量,這對政策制定者有一定啟示,因為流動性的變化通常會反映相關風險是否在累積。
作者用代數展示了流動性公式和分析框架,作者的團隊構建了一套全球流動性指數,旨在考察不同經濟體的流動性狀況,他認為這是預測外匯、債券和股市的前瞻性指標。對于配置資產而言,作者指出了流動性對金融體系的沖擊模式和傳導機制,流動性能影響投資者們的風險偏好和資產配置。當流動性充足時,違約和其他系統性風險發生的概率較低,當流動性緊縮時,市場風險偏好收縮,投資者通常轉向安全資產。作者也基于自身的投資經驗,給出了流動性處于不同階段的資產配置策略。這對投資者們應有一定啟發。
這本書值得一提的還有“金融絲綢之路”的概念,作者認為,受到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巨大投資機會的吸引,世界經濟金融的中心正在沿著“金融絲綢之路”向東移動。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增長,資本不斷向其移動,外國直接投資的大幅增長成了這些經濟體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之一。美國500強企業在引領全球資本流動方面一直處于領先地位,他們總部在美國,在紐交所上市,但會將業務外包到世界上零部件價格實惠、勞動技能強的地方,并形成了效率很高的產業鏈。
作者的分析富有洞見,近年來美國發起的“關稅戰”也正是基于這些邏輯,但作者不認為“關稅戰”是真正的命門,他認為技術卡脖子和資本流動性是更關鍵和緊要的。技術和資本的流動與商品的流動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
中國在2018年之后致力于解決關鍵技術卡脖子的問題,正是明智的做法,近年來的技術革新和相關產業發展事實也證明,這一決策非常正確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
作者也在書中指出,預計未來將出現去全球化趨勢和新地區主義,資本領域將受制于地緣政治因素。作者也認為,中國需要引進“聰明的”和追求風險的資本來保持其經濟增長和穩定,近年來中國也正在逐步取消一些對外資的限制,減少投資壁壘。另外,作者認為中國應該加大人民幣國際化的腳步,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結算。事實上,我國近年來也正在不斷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總體而言,這本書的視野超出了貨幣和流動性的范疇,看到了全球流動性背后的國家分工體系、金融體系、地緣政治等維度,正是建基于如此綜合的維度視野上,才能做到更好的資產配置。同時,作者對全球流動性的分析鞭辟入里,對不同經濟體的金融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